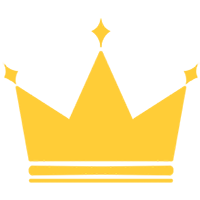 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
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幽深殿堂中,明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它既非纯粹的艺术品,亦非单纯的日用品,而是介于生死两界、沟通阴阳二世的媒介。所谓“明器”,亦称“冥器”或“盟器”,《释名·释丧制》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盐铁论·散不足篇》更直指其本质:“有形无实”。这四个字,道尽了明器千年流变中恒定不变的文化密码——它是生者为死者缔造的镜像世界,是阳间投射于阴间的光影,是“灵魂不灭”观念在最深层的物化表达。
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在那位女性遗骸的头骨旁,七颗被赤铁粉染红的小石珠静静沉睡,宛如凝固的血泪。这些精美的装饰品,是人类最早试图以“物”跨越生死界限的明证。从那一刻起,明器便开始了它贯穿中国文明史的漫长旅程。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明器种类日趋丰富,生产工具、饮食器皿、家畜谷物纷纷随葬,而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悬殊的随葬品数量——大墓一百八十余件玉器象牙与小型墓葬中一两件粗陶獐牙的鲜明对照——不仅映照出人间的贫富分化,更暗示着人们深信:那个被他们想象出来的阴间世界,同样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更有意味的是,男性墓中多见石制刀斧,女性墓中则置陶石纺轮,生者正以这些沉默的器物,将阳世“男耕女织”的理想秩序小心翼翼地移植入幽冥。
夏商时期,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明器制度与等级制度互为表里。青铜明器的出现,标志着明器从个体情感的寄托升华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四百余件青铜器,其数量之巨、工艺之精,足以令后世惊叹。而商墓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青铜酒器多置于椁内近棺之处,烹饪食器则列于椁外远棺之所——以空间的远近尺度,丈量着墓主生前的喜好刻度。殷人嗜酒,因酒亡国,而明器陈列的方式竟将这段历史凝固于幽暗的墓室之中。明器于此,不仅是阴间的用度,更是阳世生活方式的忠实记录者。
西周统治者从商朝的覆灭中汲取教训,明器世界也随之发生转向。酒器数量锐减,饪食器地位上升,商代萌芽的用鼎制度在西周被系统化为森严的“列鼎制度”。《周礼》所载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的等级序列,将礼制的丝线织入明器的经纬。然而,春秋中期以后,平民墓中开始僭越礼制出现鼎器——这些“有形无实”的青铜礼器,此时被赋予了“形有实无”的社会意涵:它成为平民阶层凭借经济实力向上攀附的文化资本,是阶层流动在墓葬中的无声宣言。
战国曾侯乙墓的一万五千余件随葬品,将明器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那六十五件青铜编钟,不仅是明器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音乐文明的不朽丰碑。它们体形庞大、铸造精良,历经两千四百年沧桑仍能演奏现代乐曲。这些沉睡地底的青铜巨匠,以其永恒的存在质问着生者与死者的界限:当明器精美至此,它是否已超越了“有形无实”的原始定义,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自身生命力的艺术创造?
秦汉以降,明器的面貌随时代流转而不断嬗变。秦代模拟生活的陶制牛车釜灶,汉代以专供随葬的模型明器取代珍贵铜漆器,魏晋南北朝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直至唐宋两朝以法律形式将明器制度完善定型——唐制规定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庶人十五事,材质尺寸皆有严格规范。这一制度化进程,将明器从民间习俗提升为国家典制,使其成为礼法体系中有形的刻度。元明清时期,纸质木质的明器渐成风尚,延续数千年的明器制度在西方科技与观念变革的冲击下逐步瓦解,清代仅以“明器从俗”四字一笔带过,至民国则“未有明器”矣。
在这漫长的流变中,几类明器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脱颖而出,成为解读中国明器文化的关键密码。
俑,是人殉制度的替代者,亦是文明进步的测量仪。从商周茅草束成的“刍灵”,到春秋战国的广泛流行,从秦代地下军阵的千军万马,到唐代歌舞胡俑的异域风情,俑的历史几乎是一部微缩的中国雕塑史与社会史。秦俑的写实雄浑、唐俑的丰腴华美、宋俑中那些奇谲的“仪鱼”“墓龙”,都以泥土与火焰凝固了各自时代的精神风貌。以俑代人的演进轨迹,不仅标示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明进步,更折射出中国人对生命价值认知的深刻嬗变。
镇墓兽,是幽冥世界的守护神。它以神兽的威仪震慑侵扰墓主的邪祟,以神话的形态安撫生者对死后世界的恐惧。这种陶质或木质的雕像,是中国人“事死如生”观念最直接的防卫性表达。
买地券与纸钱,则将阳世的货币经济完整地投射入阴间。从东汉铅板上的契约文字,到后世砖石所刻的地契文书,从剪成铜钱形状的纸钱,到锡箔制成的元宝“锡箔”,生者以这些象征物完成着与阴间的经济往来。值得注意的是,纸钱是所有明器中最具生命力的形态,直至今日,清明时节焚烧纸钱的青烟仍在许多城乡袅袅升起,仿造钞票式样的“冥钞”仍在特定店铺出售。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惯性,以惊人的韧性证明着“灵魂不灭”观念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根深蒂固。
铜镜,作为特殊的随葬明器,承载着“破暗重明”的象征功能。宋金墓葬中悬于墓室顶部的铜镜,以金属的冷光驱散死亡的黑暗。也有学者认为镜能镇邪,以防“尸气复动”。无论何种解释,铜镜都以光为媒介,在生死之间架起一座隐喻的桥梁。
明器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其深层动因根植于两个互为表里的观念体系。
其一,是源远流长的“灵魂不灭”信仰。这一观念认为,人死之后,灵魂脱离形骸独立存在,仍能干预人事、福祸生人。正是这一信念,使明器从实用器物演变为“有形无实”的象征物成为必然——既然灵魂仍需饮食起居,则必须为之备办器具;既然灵魂已脱离肉体桎梏,则器具不必完全实用。明器之“有形无实”,恰恰是灵魂之“无形有实”的镜像反映。人们以这种方式,在想象中为逝者构建了一个与阳世同构的阴间社会,并在这个虚拟社会中延续着对逝者的情感投注。
其二,是儒家“孝”观念的制度化实践。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伦理体系,儒家将丧葬礼仪提升为人伦根本。《礼记》《仪礼》乃至《朱子语类》中连篇累牍的丧葬规范,将“慎终追远”的道德律令转化为具体的器物规制与仪式程序。厚葬隆丧虽屡遭墨家“节葬”主张与个别帝王的薄葬诏令冲击,却始终是丧葬文化的主流。帝王登基伊始便着手兴建陵寝,富室巨贾倾资以求佳城——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在儒家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充分的伦理正当性。明器于是成为孝道的可视化载体,其数量多寡、质地精粗,成为衡量子孙孝心与社会评价的外在标尺。
杨树达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写道:“凡人所用明器,无不可为从葬之器云。”这句话道破了明器文化的本质特征:它是一个完全由生者依据自身生活经验与价值观念所构建的想象世界。阳世有什么,阴间便有什么;生者珍视什么,墓中便陈设什么。明器是生者投射于幽冥的社会理想,是生者抚慰死亡焦虑的文化装置,更是生者维系与逝者情感联结的精神纽带。
从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那颗被赤铁粉染红的小石珠,到民国时期渐趋消逝的随葬习俗,明器走完了它漫长的历史轮回。它从实用器物出发,演化为“有形无实”的象征物,最终又回归实用——只不过这“实用”,已从阴间用度转变为生者观赏。然而,明器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曾消逝。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物质见证,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衍变的形塑轨迹,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凝聚形态,明器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窥探古人精神世界的幽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得以看见:在灵魂不灭的信念烛照下,在孝道伦理的制度规约中,一代代中国人如何以“有形无实”的器物,构筑起一个跨越生死界限的意义世界。
这个世界虽是虚拟的,却凝结着最真实的情感与信仰。